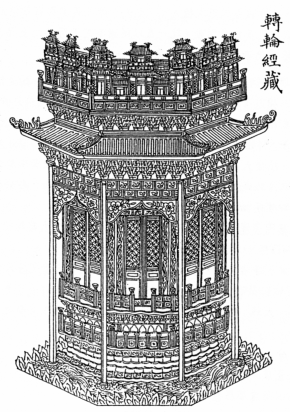
|
頁15 |
臺灣地區佛教圖書館發展之研究 |
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(2001.07) |
第二章 古代佛教圖書館經營管理之回顧
佛教自東漢時期逐漸傳入中國後,佛經即陸續翻譯成漢文,再加上漢文佛教撰述不斷地湧現,使得佛教在中國從初期的老莊格義到自成一系,並且茁壯發展成各大宗派,完全融合於中華文化思想當中。漢文佛典隨著佛教在中土的傳佈與發展,也逐漸地成長,最後形成一部龐大的漢文大藏經。基於對佛典的崇敬與教理的研究,寺院僧侶常會典藏數量眾多的經籍資料,而為有效的管理與使用,便發展出一套有系統的目錄組織與管理模式,並且同時能符合教理的發展與儀制的規範。
關於中國圖書館事業發展之歷程,盧荷生認為過去圖書館事業成功的原因,除了帝王肯定圖書館的功能,而給予充份的支援之外,還有一點值得注意,那便是從事圖書館工作的人員,有著一股無比熱誠的奉獻精神。(註1)這個原因,在過去佛教圖書館事業的發展中,亦然!我們可以發現許許多多的佛教僧眾,不管在廣搜經籍、整編經錄,或是在典藏、雕印大藏經等各方面,都是殫思竭慮地策畫經營,充滿著「續佛慧命」的使命感,令人相當感動與敬佩。而佛教圖書館事業所遺留的成果,除了在保存中華文化上功不可沒外,其完整的保存了漢文佛教典籍,嘉惠我們這一代佛弟子得以深入經藏,更是值得我們緬懷與感恩。
關於古代佛教圖書館發展的成果,學界大致上的印象都是認為相當不錯,但若要仔細舉例和說明時,則通常只有在佛經目錄方面的成就,為眾人所熟悉。早於民國初期,梁啟超就已發現經錄的突出表現,而重新給予定位,並闡明其優於傳統目錄之處,有:(1)歷史觀念甚發達:凡一書之傳譯淵源、譯人小傳、譯時、譯地,靡不詳敘。(2)辨別真偽極嚴:凡可疑之書,皆詳審考證,別存其目。(3)比較異同甚審:凡一書有同時或先後異譯者,輒詳為序列,勘其異同得失。(4)蒐采遺逸甚勤:雖已佚之書,亦必存其目,以俟采訪。(5)分類極複雜而周備:或以著譯時代分,或以書之性質分;且同一錄中,各種分類並用,給予學者種種檢查之便。(註2)對於傳統目錄學家被儒家經典束縛的缺失,姚名達更批評說:「佛書一向獨立於四部四庫之外,大藏經儼然與四庫全書立於對抗的地位,而且比它早數百年出世,並深入民間;儒家儘管排斥佛教,而佛教依然盛行,佛書依然不朽;這足見一般目錄學家拘守四部,不齒佛道的無聊,乃不合理。」(註3)
佛經目錄在前人成果相續的努力之下,終能獨樹一格,在中國目錄學上成就非凡。可是除了經錄外,古代佛教圖書館在經營管理方面的研究,似乎就乏人問津。誠如徐建華所言:「寺院藏書在規模、功用、價值、貢獻等方面,理應在中國古代
|
頁16 |
臺灣地區佛教圖書館發展之研究 |
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(2001.07) |
藏書史、翻譯史、印刷史以及教育史、學術思想史、中外交通史、文化交流史中,佔有重要的一席。然而,由於各種原因,寺院藏書至今很少為人們所認識與論及,偶有涉及,也大多語焉不詳,有明顯的隔膜之感。整個佛教寺院藏書的研究,尚處於一個層次較低的不全面介紹階段,與寺院藏書事業本身所具備的價值、貢獻地位不成比例。」(註4)學界一直鮮見涉及這方面的研究,使得古代佛教圖書館事業及發展宛如一塊沙漠之地,很少人能真正窺其堂奧,實待有志趣的學者能深入地探討和研究。
研究圖書館事業史的最終目的,是分析過去圖書館事業的特點,再進而針對當前的情勢,謀取對策,作適度的轉化,以求得到最佳的適應,作為未來發展圖書館事業的主要依據。(註5)因此,本章主要是想以圖書館事業史的角度,來探討中國古代佛教圖書館經營管理的概況;但基於篇幅的考量,並不一一敘述歷代佛教圖書館發展的情形,也不詳究所有與佛教圖書館發展有關的條件或因素,而僅就寺院藏書的內容與徵集、寺院經書的典藏方式和維護工作、寺院藏書管理的規章制度、寺院藏書的功能等四個觀點,來回顧與分析古代佛教圖書館事業在發展過程中,是如何有效率的經營和有制度的管理?這樣的分析,除了瞭解古代佛教圖書館經營的概況,開啟過去佛教圖書館光輝的史頁之外,並進一步綜合評析,作為現代佛教圖書館經營的參考依據。
第一節 寺院藏書的內容與徵集
中國歷史上的藏書事業,除了保存珍貴的文化資產外,也曾經是中國傳統社會中傳播文化的重要場所。自從雕版印刷術興盛與普及後,圖書數量大為增加,相對的藏書事業就較以往更為蓬勃發展。佛教寺院藏書即在歷代僧俗共同努力下,逐漸豐富而完善,形成以大藏經為中心的寺院藏書體系,且與官府藏書、私家藏書和書院藏書共同組成中國古代藏書事業的主體。(註6)
關於寺院藏書的濫觴,王子舟認為最早於道安撰錄時,即能肯定他所居住的寺院有經本收藏,所以客觀地說,寺院藏書是在東晉開始的,盡管此時藏書的數量不太大,但已經有了收藏、保管佛教經籍的專門藏書處所。(註7)到了隋唐時代,寺院的藏書已是非常豐富,而存放經典的處所——經藏,也就成為寺院內不可缺少的建築物之一,所以湯用彤指出:「隋唐藏經之所,想遍天下,文集中常見藏經序文,方志中所記寺廟常有藏經之院。」(註8))由於經錄的編纂嚴謹詳細,以及佛教大藏
|
頁17 |
臺灣地區佛教圖書館發展之研究 |
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(2001.07) |
經的不斷傳寫或雕印,均為寺院藏書事業的發展,奠定了良好的基礎,因此,綜觀史料中寺院藏書的各種記載,都明顯地道出古代佛教圖書館事業所展現的成果,著實豐碩傲人。
一、寺院藏書的內容
中國寺院的藏書,是僧眾參學教育的重要憑藉,也是象徵法寶的住持,所以僧侶對於寺院藏書的裝潢與貯存,向來都是十分的用心。譬如在史籍文獻中,曾敘述某些寺院的大藏經,是以金銀字書寫,裝幀高雅豪華,以顯其莊嚴;而經藏內的佈置,更是精巧細緻,金碧輝煌。此外,不少名山古剎所典藏的大藏經,有時還不止一部,經藏也不止一處。這些種種記載,都顯示了古代寺院藏書事業之蓬勃。
自古以來,有關寺院藏書內容的記載,想當然主要都是以經、律、論為主體,再加上中華僧眾的撰述所構成的。可是在眾多的史籍中,我們不難發現,一些寺院藏書的範圍,事實上並不只有佛教的經籍,而是包含了更多四部、醫方、志書乃至家譜等等非佛教圖書。(註9)例如,在高僧傳卷十四「序錄」記載,慧皎於會稽嘉祥寺作此傳記時,除了參考過將近二十種有關佛教的史傳著作外,還述說:
嘗以暇日遇覽群作,輒搜撿雜錄數十餘家,及晉、宋、齊、梁春秋書史,秦、越、燕、涼荒朝偽曆,地理雜篇,孤文片記,並博諮古老,廣訪先達,校其有無,取其同異。(註10)
由慧皎的敘述看來,嘉祥寺的藏書相當豐富,才足以提供慧皎寫作時所需的各種資料。於此,陳援庵也指出:「梁元帝撰金樓子.聚書篇,有『就會稽宏普惠皎道人搜聚』之語,則其富於藏書可想。」(註11)
另外,在續高僧傳中的「釋法融傳」,記載唐太宗貞觀年初:
丹陽南牛頭山佛窟寺,現有辟支佛窟,因得名焉。有七藏經畫:一、佛經,二、道書,三、佛經史,四、俗經史,五、醫方圖符。昔宋初有劉司空造寺,其家巨富,用訪寫之,永鎮山寺,相傳守護。(註12)
傳中云佛窟寺有七藏經畫,筆者認為是指七座書櫥,其中放置了五類圖書(註13);從這五類圖書可知,佛窟寺的藏書相當豐富,甚至連道書都有收藏。此外,傳中又言法融在貞觀十七年(643年)前,曾於佛窟寺中閱藏,且「內外尋閱,不謝昏曉」達八年之久,更證明了寺中的藏書確實汗牛充棟。
寺院所藏外學圖書中,儒家的經典較為常見,而其中值得一提的是,文人儒士的著作總集,有時也會整套收藏,這以白居易的白氏文集最為著名。東晉時,慧遠
|
頁18 |
臺灣地區佛教圖書館發展之研究 |
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(2001.07) |
於廬山東林寺建立經藏,其後雖歷經數百年,但由於「知事守固,禁掌極牢」,所以至中唐時仍然見存。白居易在「東林寺白氏文集記」中說:
昔余為江州司馬時,常與廬山長老於東林寺經藏中,披閱遠大師與諸文士唱和集卷。時諸長老請余文集亦置經藏,唯然心許他日致之,迨茲餘二十年矣!今余前後所著文大小合二千九百六十四首,勒成六十卷,編次既畢,納於藏中。……仍請本寺長老及主藏僧,依遠公文集例,不借外客,不出寺門。幸甚!(註14)
白居易與東林寺諸位長老交遊甚篤,其於寺中經藏看到慧遠與諸文人唱和的文集,因而答應諸位長老的請求,在晚年時整理了自己的詩文集,奉置於與他有緣的寺院:一部置於東都聖善寺塔院律庫中;一部置於廬山東林寺經藏中;一部置於蘇州南禪院千佛堂內轉輪經藏中。(註15)白氏文集雖非佛教書籍,但寺方仍主動徵求,並將文集置於經藏之中,足見古代寺院對於收藏外學圖書的態度,是相當開放的。此外,嚴耕望於「唐人習業山林寺院之風尚」文中則認為,由於當時除中央有秘書監、集賢書院藏書外,實無固定藏書機關,惟大寺院藏書可以恆久,故時人樂於寄藏。(註16)
白居易將其作品藏於名寺之韻事,對於後代文人多少有些啟發,也因而仿效。清嘉慶十四年(1809年),阮元仕任浙江巡撫,正值翁方綱的復初齋集即將出版,阮元乃與諸位友人論及藏書一事,或有提議說:
史遷之書藏之名山,副在京師,白少傅分藏其集於東林諸寺,孫洙得古文苑於佛龕,皆因寬閒遠僻之地可傳久也。今復初齋一集尚未成箱篋,盍使凡願以其所著、所刊、所寫、所藏之書藏靈隱者,皆裒之,其為藏也,大矣!(註17)
於是阮元在杭州靈隱寺的大悲佛閣後造立木櫥,創建「靈隱書藏」,並制定典藏條例,命二僧簿錄管鑰之。靈隱寺雖為古剎,然屢遭兵燹,在阮元設立書藏之時,寺內佛藏殘缺,不過於次年,有學人余樂土發願請購了一套嘉興藏,置於靈隱寺的蓮燈閣上,成立了經藏。(註18)因此,靈隱書藏與經藏顯然是在同一寺中,各自獨立的藏書機構。至嘉慶十八年,阮元又於焦山同樣地建立書藏,典藏條例仿若靈隱書藏,而此二書藏先後輝映,一時傳為佳話。可惜世事無常,文宗咸豐末年間的太平天國之亂,焚毀了許多圖書文獻,靈隱書藏與經藏也因而同時毀於戰火。至於焦山書藏幸好猶存,到了光緒十七年(1891年),丁丙在「焦山藏書記」中,曾敘述:
粵東梁星海太史來杭,言客歲游焦山,見書藏未毀,瑤函祕笈,如在桃花源不遭秦火。山僧尚守成規,簿錄管鑰,雖歷七、八十年,流傳弗替,可謂難矣!(註19)
|
頁19 |
臺灣地區佛教圖書館發展之研究 |
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(2001.07) |
由此看來,寺院藏書的精嚴維護與持久流傳,一直是受到文人儒士的肯定,也因此樂於將自己的著作捐置寺中,希求不朽。
寺院收藏教外的圖書,自古以來即相當普遍,至於像阮元於靈隱寺中設置獨立的書藏,有別於傳統經藏,這在寺院的藏書史中,也並非罕見。例如:北宋李常於廬山的白石庵設立了「李氏山房」,共有九千餘卷圖書,供人閱覽;南宋洪咨夔於天目山的寶福寺設立了「天目山房」,計有一萬三千餘卷的圖書。(註20)可見得,寺院除經藏外,或另設有其他藏書機構,而此現象,筆者認為應該算是寺院藏書史中的一種特殊之發展吧!
二、寺院藏書徵集的途徑
自古以來,寺院都將請藏視為開山立業之千秋大事,莫不發弘願以求之。雖然藏經的造價昂貴,而且官版藏經大多需要轉奏請旨,才得以印製,可是種種的困難卻都阻擋不了僧眾請藏供養的誓願。陳援庵於明季滇黔佛教考一書中,就曾舉出數例而言:「宮廷既有全藏之頒,林下復有方冊之刻,齎經之使不絕於途,名山之藏燦然大備。今可考見者,雞山一隅即有藏經十部,各建專室,特設知藏,所貯與書院藏書埒,或且過之,與尊經閣之常擁虛名藉培風水者,尤不可同日語。」(註21)
宋代以後,佛教典籍雕印之風氣盛行於世,而關於寺院藏書徵集的途徑,筆者考察眾多史料後,歸納分為:朝廷頒賜、私人捐置、募款請購、自行繕寫或雕印等四種。以下分別說明之:
(一)朝廷頒賜
自隋代以來,朝廷頒賜大藏經給名山古剎的記載,不絕於書。對於寺院而言,承蒙御賜官版的大藏經,乃無上之光榮,故北宋以來,天下名寺流行建碑刻載經藏記等,其原因即在此。到了明代,獲賜大藏經之佛寺者,石刻「藏經護敕」的聖旨之風,更是興盛。(註22)明英宗正統五年(1440年),永樂北藏雕成,經板歸由司禮監所管,必須奉旨才能印造。正統十年,英宗頒賜大藏經給北京法海寺、南京靈谷寺等各大寺院,而在北京法海寺即立有「藏經護敕」的聖旨碑,其碑文如下:
朕體天地保民之心,恭成皇曾祖考之志,刊印大藏經典,頒賜天下,用廣流傳。茲以一藏安置法海禪寺,永充供養。聽所在僧官,僧徒看誦讚揚,上為國家祝釐,下與生民祈福,務須敬奉守護,不許縱容閑雜之人私借觀玩、輕慢褻瀆,致有損壞遺失;敢有違者,必究治之!諭。(註23)
|
頁20 |
臺灣地區佛教圖書館發展之研究 |
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(2001.07) |
因為大藏經印造所費不貲,而全國寺院往往能獲賜者十不得一,所以獲頒大藏經的寺院,都視其為鎮寺之寶,無不建樓以藏之,立碑以記之;崇敬之情,由此可見。
(二)私人捐置
除了朝廷頒賜藏經以顯皇恩之浩蕩外,信眾捐置藏經以求佛菩薩之庇佑,亦時有耳聞,而這些記載則散見於各種史料或藏經卷後的題記中。例如於宋神宗與哲宗期間,文彥博曾撰「永福寺藏經記」,記載其捐置大藏經於所奉之墳寺:
介休空王西院、西京資聖院乃因舊院,已各有藏經,惟永福、教忠院,近特捨俸賜金帛,各置經一大藏,付逐院收掌,逐時看轉,以克資薦。(註24)
文彥博所捐置的藏經,可能就是開寶藏。(註25)在普見信眾捐置大藏經的記載之餘,偶而也會看到聖德高僧將其豐厚的供養,捐捨請購藏經的事蹟。於金石萃編補正卷四中,有李謙的「元洞林寺藏經記」一文,就記載元順帝至正年初,雪堂捐藏的偉業:
雪堂大禪師厲志勇猛,倡道有緣。……今上在潛邸,師嘗奉命持香禮江浙名藍,法航所至,州府寮屬作禮供養,日積幣賮,購所謂五千餘卷滿二十藏,為函一萬有奇;浮江踰淮,輦運畢至,凡所統十大寺,率以全藏授。(註26)
高僧雪堂以一人掌管十大叢林,並將個人所得之供養資財,請購弘法藏萬函有餘,捐置十寺,此其願力之宏廣,雖在佛門,亦可稱為大施主矣!
(三)募款請購
寫本時期的佛教典籍,主要是依靠繕寫流傳,因此寺院藏書的徵集,若非朝廷敕令與資助,往往得歷經數十餘載,才能有所規模,是相當費時與艱辛的。到了刊本時期,大藏經雖然有了迅速的出版技術,但因其印造的費用實在太高,而朝廷雕印的大藏經,始終無法獨力負擔全國寺院的請求,於是就制定請藏的經辦手續與公定價格,讓僧徒自行出資請印;至於寺院雕印的大藏經,也刊有經值劃一之目錄,以隨成本定價,便利流通。例如在大明三藏聖教南藏目錄之後,便附有明神宗萬曆三十四年(1606年),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重新制定的「請經條例」一篇,詳細制定了請藏的各項辦法。依條例之規定,永樂南藏的用紙與裝幀各分三個等級,共有九種價格,而請經僧來時先領取票號,等待印造,期間的食住費用則另計。經鋪每年約可印造二十部藏經,每部限於三個月完成,由請經僧驗收,並呈繳劄付以示優異,領取批照以便回籍。(註27)如此完善的條例,不但避免了請藏的糾紛與經鋪的弊端,亦使請經僧的權益得以保障,足見官府之用心,值得稱許。
由於請一部大藏經,要花費在印製與運送之金額相當可觀,若無獲得朝廷贈藏
|
頁21 |
臺灣地區佛教圖書館發展之研究 |
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(2001.07) |
的情況下,就算是名山古剎傾竭其資產來請購,也難有所成,於是募款請藏,就成了古代寺院常見的途徑。例如在明毅宗崇禎六年(1633年),元賢前往建州寶善庵拜謁廣印時,就曾為寺中監院欲請大藏經一事,寫疏募款云:
監院心師,思請大藏普潤群機,時有文學徐君,首發大心,揮金為倡。然大廈非一木之能搆,為山非一簣之可成,倘得同出一手,共贊嘉猷,則一文一粒,皆濁海之寶帆,而佛果之真種也。(註28)
從此疏寫作的時間推測,寶善庵想請的應是永樂南藏。誠如疏言「大廈非一木之能搆,為山非一簣之可成」,募款之事亦非一蹴可幾,因此苦募數年甚至十數載,在史料中俯拾皆是。在滇繫卷五,載清康熙年間李仙根的「迦葉殿藏經記」云:
是山有八大剎,有賜藏四,兵燹迭罹,半付劫灰。僧慧輝為破山老人四世孫,住持迦葉殿,睹其厄,傷焉,爰走姑蘇,苦募四寒暑,遂得正藏三百三十函,為卷六千七百六十,貯以十四箱,並諸佛像莊嚴以歸。(註29)
慧輝所請的大藏經為嘉興藏,雖然此藏造價比較便宜,但仍要辛勤募款四年,才能如願,因此史載其他大藏經曾募款十幾年而得,也就不足為奇了。
(四)自行繕寫或雕印
中國素有著書立說之傳統,而佛教緇素亦重視教義的撰述,作為教化之媒介。宋代以來雖有大藏經的雕印,然而佛教著作不斷產生,這些單行未入藏的書籍,就靠寺院之間繕寫流傳,或是自行雕印出版,也因此成為寺院藏書的一部份。在百丈清規證義記卷六中,就有記載「印房」一職,依其陳述內容推知,寺院出版的各類佛書,包括了:流傳廣泛的常行經典及注疏、歷代祖師的語錄和撰述等。(註30)再舉近世著名的寺院藏書——鼓山湧泉寺為例,清末民初時,該寺藏書除了歷代大藏經之外,還包括了:明、清兩代本寺高僧元賢、道霈等所著的經書,共計七千五百八十六冊,以及從宋代開始雕印的經板萬餘塊;清代手抄經書二百二十五冊,苦行僧人刺血書寫的血經六百五十七冊;印度、緬甸傳來的貝葉經七冊。陳錫璋即指出,鼓山經籍之多,為海內所無,堪稱為一座佛經的寶庫。(註31)
第二節 寺院經書的典藏方式和維護工作
在古代,藏書固然不易,而入藏後若不加整理編帙、庋藏列架以便取閱,則無異雜紙一堆。至於藏書事業想要維持長久,則有賴良好的藏書管理,亦即完善的制
|
頁22 |
臺灣地區佛教圖書館發展之研究 |
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(2001.07) |
度與確實的執行。換句話說,舉凡編目、合帙、庋架、閱覽,乃至防蟲、除黴、曝曬、修補,都是繁瑣而持續的工作,需要詳密的規章制度與持之以恆的精神。古代佛教圖書館事業的發展,不僅在佛經目錄、組織整理與收藏數量方面,均有不錯的成績,甚至在典藏借閱的制度與管理方面,那更是令人刮目相看,尤其是寺院清規中對於藏書管理的各種辦法,制定鉅細靡遺,以及使用「千字文」作為排架的序號等,都與今日圖書館的管理制度有著許多異曲同工之處,實在叫人佩服先賢的智慧與用心。
一、大藏經帙號法的演變
中國古代藏書發展的歷程中,由於經典卷數越來越多,易致散亂,因此發明將約十卷的經書合為一帙,以便於庋藏與取閱;佛經庋藏的方法,亦是如此演變,所以每部經卷庋藏時,都是以帙為單位來管理。可是,如何透過目錄有秩序的庋架,即成了庋藏工作的重要關鍵,需要研發專門的方法,以使在茫茫的書海中,迅速找到想要的書籍。有關大藏經帙號法的演變,方廣錩根據敦煌文獻的各種記載,考證出大藏經標誌的方法,先後出現了:經名標誌法、經名帙號法、偈頌帙號法、千字文帙號法等類型,分別略述於下:(註32)
(一)經名標誌法
經名標誌法是在大藏經合帙後,出現的一種標誌法,即是以帙中的某經名來標誌該帙。若一部經分作多帙或自成一帙,以經名來標誌是直接而無問題的;但若多部經合成一帙,則標誌時均只標出該帙第一部經的經名,並註記該帙的總卷數或部數。此時,經錄或帙皮上出現的經名,實際上代表的只是這部經所在的那一帙。
(二)經名帙號法
經名帙號法是在經名標誌法的基礎上,另行發展的一種佛藏帙號標誌法。當遇到多部經合成一帙時,經名標誌法對於該帙已失去意義,所以乾脆予以簡化,將用作標誌的經名,擷取其中某一單字當作帙號。擷取時並無一定的標準,但必須與之前已取做帙號的字互不重複。這樣的標誌法,方廣錩命名為「經名帙號法」。
此外,由於經名標誌法與經名帙號法的缺點為無序,是無法反映出本帙在大藏經中的位置。為了要配合經名標誌法與經名帙號法來庋藏大藏經,故另有「定格貯存法」的產生,即於經錄上清楚地記載每帙在經櫥中貯存的位置。在道宣內典錄.
|
頁23 |
臺灣地區佛教圖書館發展之研究 |
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(2001.07) |
入藏錄中,有著關於當時西明寺經藏所用定格貯存法的完整記錄,其並於錄前云:
依別入藏,架閣相持,帙、軸、籤、牓標顯名目,須便抽撿,絕於紛亂。(註33)
這段敘述,清楚說明了當時經藏的庋藏,是將經名標誌法或經名帙號法與定格貯存法相互配合著使用,以使佛藏的管理井然有序。
(三)偈頌帙號法
偈頌帙號法是採用佛教的偈頌,作為大藏經帙號的一種方法。由於經名帙號法中,帙號與帙中的佛典不再有直接的關係,於是提示了僧人可以改用另一種有序的帙號來代替。在敦煌文獻中,可以看到僧眾利用當時常念誦的一些偈頌,刪除其中重複的字句,來作為大藏經帙號。這種新帙號本身雖與帙中佛典的內容無關,但由於它是有序的,可以反應該帙在整部大藏經的位置,從而提示出帙中佛典的內容。
(四)千字文帙號法
所謂千字文帙號法,即是以「千字文」來作大藏經的帙號。「千字文」是一篇由一千個不重複的字所寫成的文章,四字一句,押有韻腳,內容包括簡要的天文地理、人事倫常、立身處世、慎言勸善等觀念與行為,為古代童蒙教育的讀物之一。由於大藏經需要有序的文字作為帙號,且數量高達五百種字以上,佛教偈頌自然無法承擔此一任務,而「千字文」自南北朝以來,流傳相當廣泛,識字者都會背,恰能符合大藏經帙號的需求,於是在晚唐至五代之際,千字文帙號法就逐漸傳佈開來,一直到清朝,歷代沿用不衰,成為漢文大藏經唯一的標誌法。
關於千字文帙號法是由誰發明的?自古以來,學者們均認為是開元錄的作者智昇所創,此乃因為在大藏經中,有部經錄名為開元釋教錄略出,內容以開元錄.入藏錄為底本,並增編了經典譯著者的姓名與千字文的帙號,而此錄所登記的作者亦為智昇。然而方廣錩認為,略出所記載各部經的紙張數與卷數,與開元錄.入藏錄所記載的多少有些出入,顯然此二錄所根據的不是同一部大藏經,於是透過各種史料分析考證,認為略出非智昇所作,千字文帙號法亦非智昇所發明。(註34)雖然千字文帙號法的真正發明者無從得知,但方廣錩卻進一步考證,推測千字文帙號法產生於會昌廢佛後的晚唐時期,而五代時已在全國各地廣泛地流傳。(註35)
王重民認為,千字文帙號可說是我國最古老的排架號與索書號,故知在八世紀初葉,我國圖書館在藏書和取書上的技術,已經達到相當科學的程度。(註36)方廣錩亦指出,這是我國古代僧人的一大創造,是漢文大藏經管理制度上的一大突破,同時,這也說明我國晚唐時圖書館在管理的技術上,已經達到了相當科學的地步。
|
頁24 |
臺灣地區佛教圖書館發展之研究 |
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(2001.07) |
(註37)由繁化簡,從無序發展成有序,「千字文」終使大藏經的組織與帙號緊密地結合,而庋藏與排架的工作也因此有了依據。當刊本大藏經開始雕印後,為使所刻各板片不致錯亂,千字文帙號甚至還刻在每塊經板的版首與中縫處,成為刊本大藏經頗具特色之處。
二、寺院藏書的維護工作
書籍聚散無常,輾轉流傳間,難免會受到不同程度自然或人為的毀損。明代高僧袾宏所撰雲棲共住規約附集中的「藏經堂事宜」,即開宗明義說:
諸方藏經所以久而散失,以至壞滅者,其故有二:一者借出,謂借者或不能切切送還,管者又不能勤勤取討,年月漸深,不知誰借?其故一也。二者失管,謂應曬時不曬,取出時不記帳,收入時不勾銷,看閱時不細行展卷安頓,其故二也。(註38)
因此元代德煇重輯的敕修百丈清規卷四「知藏」條中,說明知藏必須要克盡其職:
函帙目錄常加點對,缺者補完,蒸潤者焙拭,殘斷者粘綴。(註39)
故知古代僧侶對於寺院藏書,會定期查點和曝曬,若發現有黴斑與蠹痕,則立即撿出修補,如此才能與其他典藏管理的方法配合,妥善維護藏書的完整。
在查點與修補藏經的例證上,方廣錩於「敦煌藏經洞封閉原因之我見」中說:「從現存敦煌遺書可知,敦煌寺廟經常清點寺內的佛典與各類藏書,現已發現各種清點記錄共三十多號。清點佛典與藏書,無非是查看有無借出而沒有歸還的,有無殘破而不堪使用的。若有未歸還的,則須抓緊催還,敦煌遺書中存有幾件催還狀,正是這種活動的實錄;若有殘破的,經修補可繼續使用者,則修補之。……而那些殘破不堪使用的,則須將它們從藏書中剔除,並視需要而進行相應的配補。敦煌遺書中存有一批配補錄,就是這種活動之證明。」(註40)至於藏經修補的工作,最困難之處在於預算不足,因此若囿於經費而無法修補時,寺僧則會寫疏募款。例如明神宗萬曆初年,杭州上天竺講寺曾寫疏勸募修補御賜藏經,曰:
奈何歲月既久,不免蠹魚交侵,碎金不止二三,完璧僅存六七。念國璽之全書既毀,矢山門之缺典重新,先須有餘之財,庶補不足之數。遍叩高賢共成勝事,一卷、兩卷請隨緣而繕寫,三函、四函更量力以助裝。(註41)
然而藏經查點與修補的工作,寺院住持的態度尤為重要,百丈清規證義記即說:
脩整經典,乃表敬法寶,此事係慧命攸關,故此執亦為一寺重任,而尤要在住持不惜貲費,則脩整為易,即執事之人,亦因之而慎重矣!(註42)
|
頁25 |
臺灣地區佛教圖書館發展之研究 |
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(2001.07) |
可見不論圖書館的技術與服務如何運作,若無其母機構能全力的支持與配合,則一切理想均為空談,古今皆然。
在曬書方面,我國漢唐時期即有曝書活動的記載,可謂流傳已久,因此寺院僧人曬書的時間和方法,與民間的傳統差別不大。例如雲棲共住規約中說明:
六月曬經,但取晴明,不必拘定初六。每曬一百函,不得多少。近山廚,九月再曬一次。(註43)
理安寺志卷六的「箬菴禪師兩序規約」中,則說明:
每年夏季六月,鋪齋棹二十張,先曬東櫥,後曬西櫥,候冷收櫃。(註44)
夏至後的伏天,氣候乾燥炎熱,通常是一年之中最適合曬書的季節,不過因各地風土氣候和書櫥位置的不同,也會有些差異,所以祩宏才說「不必拘定初六」、「近山廚,九月再曬一次」,充分瞭解曬書一事也須因時因地而隨機應變。至於書籍曝曬後,不能立即放回櫃中,是因書頁中的水分多已蒸發,須待其涼透,回吸部分水氣之後,紙張才不致變得焦脆易裂,墨色也才不易變質。而且尚存餘熱的書冊收回櫃中,溫度累積昇高,會促使蠹蟲更加活躍,反而造成更嚴重的書傷。(註45)
除了曬書外,在近世出版的金山規約、高旻寺客堂規約中,則是以翻經的方式進行防黴的工作。翻經的時間選擇與曬書相同,而進行的程序則為:
天氣晴穩,聽和尚招呼,客堂挂翻經牌,……班首領班到藏經樓,依次第坐下,僧值即派識字七八人,開櫃下經。……放法,一桌三函,函直擺,函頭邊字對翻經人。經翻過,即理清楚,橫放桌邊,收經人見有橫放者收之,無函者放之。下經未翻不能橫放,下經之人放經不能橫放,要緊!(註46)
翻經之日,寺院僧侶全員出動,都要更衣淨手,並用特製的竹片,一頁一頁地輕輕翻動。至於翻經的目的有三:(1)使佛經紙頁能夠與乾燥空氣充分的接觸,達到去濕之目的。(2)全面檢查佛經保護狀況,一旦發現蟲蛀、霉菌痕跡,隨即隔離,進行處理,以防後患。(3)對佛經裝具進行安全檢查和衛生清掃,清除隱患。(註47)
第三節 寺院藏書管理的規章制度
一、寺院藏書管理職務之沿革與職責
當造立經藏的風氣普遍盛行後,專門負責管理經藏的職務也就應運而生。在本章第一節提到梁武帝於華林園總集佛典,並敕令寶唱掌管寶雲經藏,因此寶唱可說
|
頁26 |
臺灣地區佛教圖書館發展之研究 |
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(2001.07) |
是史載政府所設立的佛教圖書館館長第一人。另外在續高僧傳卷十二「釋慧覺傳」中,也記載隋煬帝即位後,旨令慧覺掌理寶臺經藏的「知藏」一事。(註48)此外,方廣錩根據敦煌文獻的記載,指出唐代敦煌寺院管理經藏的機構叫「經司」,而經司的管理人則稱「知經藏所由」。(註49)從這些零散的史料可知,經藏管理的專門職務早在南北朝時已產生,只是早期職務的名稱並無一致而已。
初期中國的寺院制度,基本上為佛教戒律的延伸,並配合實際運作情形,做大略的職責分工。後來寺院規模越來越大,僧眾數量亦越來越多,於是管理寺院生活的辦法,也因需求而制定。在唐代,禪宗逐漸興盛,然而禪僧以道相授,多岩居穴處,或寄住律宗寺院,尚未營立禪寺。中唐時禪宗名僧懷海於百丈山別立禪院,且認為禪僧住在律院尊卑不分,說法住持和修行生活也不合規制,因此根據中土國情和禪宗特點,折衷大小乘戒律而制定清規,開創了中國佛教的叢林制度。(註50)因懷海成名於百丈山,故後人稱為「百丈禪師」,稱其制定的清規為百丈清規,或是古清規。自會昌法難之後,禪、淨以外諸宗均面臨「斷簡殘篇,學者無憑」的困境,禪宗因此盛行於天下,後世教、律等各宗寺院則亦仿效禪林制度,各種因時因地制宜的祖訓師說,就取代了傳統寺院所持的戒律。百丈清規完全表現出中國化的寺院生活,其普遍性不但為佛教各宗所遵循,甚至也影響了道教宮觀與儒家書院的規制,成為遠東一般宗教社團的準繩,在歷史上具有特殊的意義。(註51)
百丈懷海制定清規之後,隨著叢林與社會的互動和發展,叢林制度進一步修訂,到宋徽宗崇寧二年(1103年)時,宗賾為了復興百丈的古清規,制定符合時代的叢林生活規範,於是遍訪十方叢林,網羅種種規範,撰成了禪苑清規。古清規於元代時早已不傳,而禪苑清規則是目前現存最早的一部清規,就其內容來看,北宋時期叢林制度已燦然大備,南北普遍流行。至於古清規的原始風貌,學者們認為可從「禪門規式」一文中,略窺大概。在「禪門規式」中提到設立「十務」負責叢林的營運,表示出叢林職務已有完善的責任分工,至於「十務」的內容,則無詳細述及。宇井伯壽和佐藤達玄均認為,若參照禪苑清規所規定一山的營運,為四知事與六頭首的合議制,這很可能就是源自於古清規的「十務」。(註52)由於在六頭首之中有「藏主」一職,故可推知最遲在百丈的時代,經藏管理一職的名稱,就逐漸統一以「藏主」來稱呼,且沿用至清代。
然而,以「藏主」來稱呼經藏管理人並非一成不變,在宋代有些禪宗語錄中,也看到以「知藏」來稱呼,日僧無著道忠於禪林象器箋上冊「知藏」條的解釋,亦為:「即藏主也。」(註53)可見藏主與知藏二詞,於宋元時期是同一意思,應無區分。不過到了清代以後,藏主與知藏似乎有了職責的劃分,以同樣對「知藏」的說
|
頁27 |
臺灣地區佛教圖書館發展之研究 |
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(2001.07) |
明,在儀潤百丈清規證義記所引用的版本,解釋為:
知藏,兼通義學;藏主,乃其所屬,須協衷保護經藏。凡函帙安置、修補殘缺,以及經本出入等事,俱知藏總其綱,而藏主分其執也。藏主執經櫥鑰匙,凡經書不借出以山門為限。(註54)
由此看來,知藏即圖書館的館長,而藏主就是其館員了。
不管經藏管理一職的稱呼與分工如何演變,有關其職責的內容,自古以來卻似乎變易不大。在清規成立之前,有關經藏管理的各種文獻,除敦煌文獻外,鮮有記載下來,最多只有零星數言而已。例如白居易曾敘述其新修香山寺經藏堂之經過:
於諸寺藏外雜散經中,得遺編墜軸者數百卷帙,以開元經錄按而校之,……合是新舊大、小乘經、律、論、集五千二百七十卷,乃作六藏,分而護焉。寺西北隅有隙屋三間,土木將壞,乃增修改飾,為經藏堂。堂東西間闢四窗,置六藏,藏二門,啟閉有時,出納有籍。堂中間置高廣佛座一座,……環座懸大幡二十有四,榻席巾几洎供養之器咸具焉。(註55)
從上述可知,白居易是將六座經櫥置於經藏堂的東西窗邊,而堂中央供有佛像,堂內並設有几席,應該就是作為閱覽之用的。而「啟閉有時,出納有籍」,和上述白居易於「東林寺白氏文集記」中說「不借外客,不出寺門」等,都是最基本的借閱管理之規則。另外,方廣錩從敦煌文獻的相關記載中,考證出唐文宗年間敦煌佛藏的管理制度,為敦煌諸寺既有本寺的經典,又有公用的官經,官經存於龍興寺,由經司所由負責管理。僧人們為轉經、抄經所需,可向官經借本,從所由辦理借經手續。所由應催促借經人及時歸還所借經本,並且經常點勘藏經,若發現有損壞與缺失等情形,應及時配補。(註56)
至於宋代以降,各種版本清規所記載的藏主職責,幾乎是大同小異,因此筆者選擇條序分明的清規,即明代通容撰述的叢林兩序須知,錄其內容作為代表:
藏主須知:經藏輝煌,佛祖命脈所寄也。司其柄者,貴乎勤謹小心,以護持聖教為念。若夫几案不嚴、喧煩不息,則非藏主待眾之道矣!……
一、藏內所有經典,宜敬重。
一、藏內經典宜照字號次第安放,以便尋覽。
一、藏內經典函帙若干、安放某處,宜置總簿記定,以便查閱。
一、藏內經典溼潤蠹壞,須照顧晒焙及時。……
一、藏內所有經典函帙目錄,常加點對,有殘斷缺失者,須粘綴增補之。
一、藏內經典眾有請出披閱者,宜然名登簿,及閱畢送還,仍照簿交收入藏,毋致散失。
|
頁28 |
臺灣地區佛教圖書館發展之研究 |
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(2001.07) |
一、職掌藏內經典,亦宜用心博稽,廣其聞見,毋徒目為故事。
一、經藏鎖鑰,須嚴謹。
一、潔淨藏堂,及嚴拭几案等。
一、凡方丈所囑大小事物,行之果否,當回覆。
一、處眾貴寬和,不得恃職亢上凌下。
一、各寮執事巨細相通,不得別戶分門,妄生彼此。
一、不得大小諸寮,干涉餘事,除公務告請會議者。
一、本寮所有常住物件,宜私自登簿,以便查考。
一、退職日,將本寮常住物件并藏內經典函帙,照號對簿,簡點分明,交與新藏主掌管,毋混亂。(註57)
從藏主的這些職責,吾人可窺知古代寺院經藏的經營管理,從排架、編目、維護,乃至職務上的應對與交接,都已具有規模和制度,而其精神更是值得現代佛教圖書館所學習。
二、寺院清規中之借閱規則
寺院清規對於除了對藏主的職責有著詳細的說明之外,對於僧眾借閱經書的方法,也有完善的制定,而其中隨著時代的變遷亦有些許的差異。首先從現存最早的清規,即宗賾所編集的禪苑清規看起,有關當時借閱經典的方法為:
請案之法,先白看經堂首座,借問有無案位,欲來依棲。如有案位,即相看藏主白之,茶罷,藏主引至經堂案位前,各觸禮一拜。……相看殿主,乞依時會經,並無拜禮。早晨大眾起、晚間放參前,殿主鳴鐘會經,交點出納。會經僧應於藏內燒香禮拜,殷重捧經,路中不得與人語笑。……堂中不得接待賓客,有人相訪,默揖歸寮,亦不得於看經窗外與人說話,恐喧大眾。……看經時端身正坐,不得出聲及動唇口,並緣他事。……如欲退案,亦先白看經堂首座及藏主,還經入藏,方可如意。已上所說並當藏主曉諭眾人,若不如法,方便開示。(註58)
從上述可知,藏主如同今日圖書館館長的地位,看經堂首座則是閱覽部門的負責人,而藏殿殿主職掌的就是流通部門,可見宋代寺院經藏的運作管理,相當完備。至於文中述說禮拜的儀式與各種禁令,均顯示出僧眾對於經教的恭敬態度,以及注重閱覽環境的整潔與安寧,這相較於現代圖書館閱覽規則的精神,是不分軒輊。
此外,戴儉於禪宗寺院建築布局初探書中更指出,從上述禪苑清規的引文推
|
頁29 |
臺灣地區佛教圖書館發展之研究 |
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(2001.07) |
知,宋代的經藏是由藏殿與看經堂兩部份所組成,前者專供收藏,後者專作閱覽,且兩者建築分立,但相距不遠。這又從現存於日本東福寺的大宋諸山圖中,天童、靈隱二禪寺的建築布局,亦是清楚地畫出看經堂與藏殿為兩個獨立的部份,可資佐證。(註59)然而這樣的建築模式到南宋中葉以後,逐漸有了改變,敕修百丈清規卷四中記載著:
凡看經者初入經堂,先白堂主,同到藏司相看,送歸,按位對觸禮一拜,此古規也。今各僧看經多就眾寮,而藏殿無設几案者。……若大眾披閱,則藏主置簿,照堂司所排經單列名,逐函交付。看畢,照簿交收入藏,庶無散失。(註60)
可見元代以後,看經堂建築已不復存在,僧眾逐漸改以借回寮房閱覽。至於禪苑清規中記載借閱時的各種儀式,則簡化或消失,其後各部清規中已無相關的說明。雖然借閱時不再依循舊規的儀式,但在寮房中閱覽經卷的規矩,仍然相當嚴謹。例如宋寧宗嘉定二年(1209年)宗壽編的入眾日用中,就說明在寮房中的閱覽規則:
茶罷,或看經,不得長展經,謂二面也。不得手托經,寮中行不得垂經帶,不得出聲,不得背靠板頭看經。古云:「出聲持誦,吵噪稠人;背靠板頭,輕欺大眾。」(註61)
正襟危坐默閱經典,有利於靜心專一,並展現出僧眾嚴以律己以成就道業。
由於借閱時的儀式簡化,所以借閱的規則就剩下登記事宜。例如在儀潤的百丈清規證義記中,只說明著:
凡請看者,須登牌:某月、某日,某人請某字函經;還則消賬。若其人告假并餘事欲去者,先查取;遺失者,罰抄賠已,出院。(註62)
出院,是相當嚴厲的懲罰,足見寺院對於藏書維護之重視。至於上述提到了關於遺失賠償的處理方式,使人聯想到在其他清規中,是否有清楚地規定違規處罰的方法?在雲棲共住規約中,就有訂定一些違反借閱規定時,管理者的罰則:
一、經不借出,以山門為限。雖朝借暮還,亦決不借。借出,罰銀三兩。……
一、看取即記簿:某月、某日,取某函,某人取;後空一行,待收入時填寫。失寫,罰銀一錢。
一、開廚取經及入經訖,即鎖。失鎖,罰銀一錢。(註63)
以上是針對經藏管理者失責的處罰,以提醒管理者時時小心維護經書。不論在賠償或罰則的內容上,古今處理的態度上,多少有些雷同之處,足見如何有效地維護館藏的完整性,一直是圖書館經營者所關注的焦點。
|
頁30 |
臺灣地區佛教圖書館發展之研究 |
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(2001.07) |
第四節 寺院藏書的功能
由於古代書籍的傳寫、雕印與保存不易,因此寺院藏書的主要任務,自然就是使法寶長存,這是毋庸置疑的。在典藏經書的任務之餘,寺院藏書相對也提供了僧侶修學、撰述參考等多項功能,於是筆者歸納了寺院藏書的功能,有如下四點:
一、僧眾修學和閱藏
自古以來佛教義理的研究,一直是僧徒修學佛法的主軸之一,因此古代寺院的藏書,自然是以提供僧眾修學與閱藏,為最主要的功能。在上述寺院清規中關於經藏借閱規則的制定,即能證明歷代僧眾時常借閱寺院的藏書,以研習教義。至於在僧眾閱藏方面,由於大藏經的卷帙浩瀚,義理深遠,通常若想完整有序的讀完一部大藏經,是需要有個良好的環境,且心無旁騖花上一、兩年以上的時間,才得以如願。於是有些寺院除經藏建築之外,還另闢閱經樓,並提供食宿,讓專門前往閱藏的僧人有個清幽無虞的環境,可以專一深入法海。清代儀潤在百丈清規證義記卷五中,即建議說:
凡有藏經之處,宜供一閱藏之僧,使其日日翻閱看誦,即是法輪常轉,誠為叢林吉祥善事,又有益於學人,倘其日新有功,即可延佛慧命,豈不美哉!(註64)
例如近代高僧釋太虛於自傳中述說,清末時曾赴慈谿汶溪西方寺閱藏,安居在藏經樓的閱藏寮中,當時閱藏寮總共有八間,並在藏經樓另開飯一桌,而寺院中的各種作息盡皆不用去。(註65)可見寺院對於能夠閱藏的僧人,都是相當敬重禮遇的。
另外,由於寺院中多少藏有佛典以外的圖籍,因此曹仕邦在中國沙門外學的研究中便指出,中國僧人研習外學的首先刺激,就是寺院中的藏書,其次則是寺院本身也鼓勵沙門兼習外學,所以出家人中對學術有興趣者,自然於暇時批閱經史之類的典籍;這從歷代僧傳中,教外學養豐富的僧人不勝枚舉,可資證明。(註66)
二、僧人撰著之參考文獻
在佛教大藏經中,有關中華僧人的撰述,除了佛經目錄、經本要抄外,還有類書、法數、音義等工具書,以及祖師法集、語錄等集成,其中二、三十卷以上的大作比比皆是。寺院僧眾在圖書齊全的環境中,往往學問淵博,著作等身,例如前述
|
頁31 |
臺灣地區佛教圖書館發展之研究 |
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(2001.07) |
慧皎撰述高僧傳時,是參考利用會稽嘉祥寺的眾多藏書而成的,故知寺院藏書的功能之一,就是在僧人著作之時,提供了豐富的參考文獻。而利用豐富的藏書展開撰述的工作,也反應出寺院藏書在佛教文化活動中,是不可或缺的關鍵所在。
三、教徒崇信與寺院經濟的來源
古代寺院的藏書,從一開始便具有兩種意義:一是提供寺內僧人閱覽的實用價值,二是經典的神聖性促使信眾與僧人的崇敬禮拜。由於大乘經典時常強調讀經閱藏的功德無量,這種教義思想深植人心,促使了寺院藏書與宗教信仰活動的結合。自古至今,佛教的許多法會活動,就一直以誦讀某幾部經典為主要的模式,而透過法會的舉行,即成為寺院經濟收入的來源之一。
在宋元時期,更有一種與寺院藏書關係密切的法會活動,就是信徒供請僧眾閱讀整部大藏經。禪苑清規卷六「看藏經」一文,即詳細記載這個法會進行的內容:
如遇施主請眾看大藏經,……至時維那鳴鐘集眾,請經依位坐,法事聲螺鈸,知客點淨,引施主行香竟,當筵跪爐,維那表歎,宣開啟疏,念佛闍梨作梵,候聲絕,然後大眾開經。……如施主於看經了日,設齋供慶懺,更須讀罷散文疏,施主經錢並係堂司取掌分俵。……如不能看經,即於堂司退免;若已受經,即須子細如法披尋,早了為上。(註67)
另外在玉岑山慧因高麗華嚴教寺志卷七中,有「捨田看閱大藏經誌」一文,為元仁宗延祐四年(1317年),杭州官員吉剌實思誌曰:
自揆庸才,得沾玄化,念四恩之至重,憫群迷之未覺,謹以中統鈔三百定規置田土,捨入天竺、高麗、淨慈三寺各一百定。歲以一月為約,命僧繙閱三乘妙典一大藏,所集殊勳,上以祈國家之福,下以報父母之恩,旁資眾有共成正覺。……
誦經月分
上竺天臺靈感觀音教寺 正月
高麗慧因高麗華嚴教寺 五月
淨慈報恩光孝禪寺 九月(註68)
可見宋元時期,看藏經法會相當普遍,應是寺院理想的資金來源。然而明代以來卻逐漸失傳,至今鮮為人知,筆者推測其原因,或許是明清時期佛教衰弱,僧侶大多學識不足,若靠少數幾人,實難如期閱完整部藏經。
由寺院藏書發展成宗教信仰的活動中,除了看藏經法會外,還有屬於輪藏的信
|
頁32 |
臺灣地區佛教圖書館發展之研究 |
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(2001.07) |
仰活動最為顯著。輪藏為轉輪經藏的簡稱,或稱大藏,造型通常為八面立體式可轉動的經櫥,宛如超大型的旋轉書架。輪藏主要以一大軸貫穿其中,下設機輪,若人來推動,則能運轉,象徵法輪的轉動;藉轉動一匝,恰似將輪藏上的佛經抄寫或唸誦過一遍,其作用可為死者求冥福,為生者求安樂,因此輪藏有時也稱為「壽山福海」。(註69)輪藏的工藝精巧,製作奇特,而其建築的結構,大都是按照北宋時李誡編修的營造法式中所規定的比例建造。該書的卷十一「小木作制度」與卷二十三「小木作功限」中,詳記輪藏各部份尺寸大小及造作功數,卷三十二並有繪圖,以供後人據以製造。(見圖2-1,(註70)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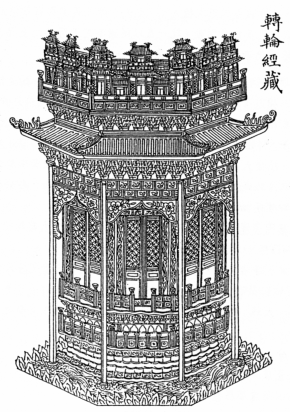
圖2-1 轉輪經藏圖
關於輪藏的起源,自古以來來均認為是梁時傅翕(善慧大士)所創。在唐代樓穎撰的善慧大士錄載云:
大士在日,常以經目繁多,人或不能遍閱,乃就山中建大層龕,一柱八面,
|
頁33 |
臺灣地區佛教圖書館發展之研究 |
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(2001.07) |
實以諸經,運行不礙,謂之輪藏。仍有願言:「登吾藏門者,生生世世不失人身,從勸世人有發菩提心者,志誠竭力,能推輪藏不計轉數,是人即與持誦諸經功德無異。」(註71)
對此傳說,張勇做了詳盡的考證,認為無疑,並進一步指出,由於傅翕少年失學,對於文盲之苦的體會定當頗深,故其成道後,欲使無識文斷字能力的黎庶能參預閱藏,於是晚年時在松山雙林寺,創建了「與持誦諸經功德無異」的輪藏。(註72)
明顯地,輪藏發明的最初目的,就是為了讓人人都有轉經閱藏之機會,而特設的方便之門;傅翕的願心與巧思,令人讚歎。因為輪藏本身就具有儲經的功能,所以佛寺藏書的處所,有時就以輪藏的造型呈現。唐中葉以後,寺院逐漸興起建造輪藏的風氣,到了宋元時期,輪藏已經成為佛寺,特別是禪院的必要建築。王子舟指出,由於輪藏櫥內存放的大藏經只是一種象徵物,並不是供人閱讀的,當信眾虔誠的推轉輪藏時,這些藏經就被塗上一層莊嚴的色彩,與佛像一樣,共具受人禮拜的功能,使得本來具有學術意義的藏書活動,轉換成宗教信仰的活動。(註73)輪藏的發明,讓經典的崇敬禮拜有了具體的形象與活動,但南宋著名的藏書家葉夢得,於「健康府保寧寺輪藏記」中言:
吾少時見四方為轉輪藏者無幾,比年以來,所至大都邑,下至窮山深谷,號為蘭若十而六七,吹蠡伐鼓音聲相聞,襁負金帛踵躡戶外,可謂甚盛;然未必皆達其言,尊其教也。施者假之以邀福,造者因之以求利,浸浸日遠其本。(註74)
由「施者假之以邀福,造者因之以求利」此段話,顯見宋代以後輪藏信仰的演變,已成為寺院營利的項目之一。關於此點,黃敏枝於再論宋代寺院的轉輪藏中更說明,由於信徒轉動輪藏是需要支付一定的費用,所以宋代寺院均汲汲於建造輪藏以邀厚利,而寺僧的日常粥食之費就可以靠論藏來解決。又為了吸引信徒的眼光,輪藏的建造無不極盡工巧之能事,除了富麗堂皇外,還有各種雕飾,以及加上音效、煙火等特殊效果,已廣耳目之娛。(註75)在利之所趨下,寺院的藏書單位竟能成為純粹的營利機構,實在是傅翕創設輪藏時始料未及的發展。
四、文人儒士讀書之場所
自古有關文人儒士寄讀寺院的記載俯拾皆是,例如梁書卷五十述說:
劉勰字彥和,……早孤,篤志好學,家貧不婚取,依沙門僧祐,與之居處積十餘年,遂博通經論。(註76)
|
頁33 |
臺灣地區佛教圖書館發展之研究 |
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(2001.07) |
儒生讀書於寺院的風尚,到了唐代更是盛行,對於這個現象的成因,嚴耕望在「唐人多讀書山寺」一文中分析認為:「名山巨剎既富書藏,又得隨僧齋飧,此予貧士讀書以極大方便。當然政府不重教育,惟以貢舉招攬人才,故士子只得因寺院之便聚讀山林,蔚為時風,致名山巨剎隱然為教育中心之所在。」(註77)
至明代,儒生讀書於寺院的風氣依然不減,陳援庵於明季滇黔佛教考中,亦指出:「讀書僧寺,恆事也。……元明以來,滇黔初闢,多未設學,合全省書院學宮之數,曾不敵一府寺院十之一,……此滇黔寺院所以眾也。學宮書院為後起,且多在城市,不在山林,潛修之士,輒惡其囂俗;惟寺院則反是,即在城市,亦每饒幽靜之處,故人樂就之。」(註78)今以徐霞客遊記為例,其文中常可見到儒生讀書於僧寺的記載,甚至有一次,徐宏祖來到雲南昆明的玉案山筇竹寺,遇到方丈體空的懇留言:
此亭幽曠,可供披覽;側有小軒,可以下榻;閣有藏經,可以簡閱;君留此過歲,亦空山勝事,雖澹泊,知君不以羶來,三人卒歲之供,貧僧猶不乏也。(註79)
從體空的這段話,亦可見寺院的藏書,乃是吸引文人書生來寺讀書的條件之一。
總結以上寺院藏書功能的歸納和分析,得知古代佛教圖書館事業的發展,除了在典藏管理之技術層面上有卓越的成就外,在書籍的閱覽利用上,也並非完全如傳統印象中為束之高閣,僅作典藏供養之用而已。特別是在寺院藏書發展的歷程中,值得再次提及的,即運用佛教徒對於經典的崇敬態度和功德信仰,而演化出與寺院經濟相結合的法會活動,此現象非但為寺院藏書活動中的一大特色,亦可說是我國藏書史上,相當特殊的應用展現,值得學者們更進一步來探討和研究。
|
頁35 |
臺灣地區佛教圖書館發展之研究 |
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(2001.07) |
註 釋
註1:盧荷生,中國圖書館事業史(臺北市:文史哲,民75年),頁12-13。
註2:梁啟超,「佛家經錄在中國目錄學之位置」,張曼濤編,佛教目錄學述要,現代佛教學術叢刊40(臺北市:大乘文化,民66年),頁21。
註3:姚名達,目錄學,人人文庫1652、1653,臺三版(臺北市:臺灣商務,民69年),頁111。
註4:徐建華,「中國古代佛教寺院藏書若干問題研究」,黃建國、高躍新合編,中國古代藏書樓研究(北京市:中華書局,1999年),頁79。
註5:同註1,頁200。
註6:同註4。
註7:王子舟,「公元四世紀東晉:佛教藏書的濫觴」,內蒙古圖書館工作1990年4期(1990年11月),頁28-30。
註8:湯用彤,隋唐及五代佛教史(臺北市:慧炬,民75年),頁125。
註9:同註4,頁94。
註10:(梁)釋慧皎撰,高僧傳,卷14,大正新修大藏經,第50卷史傳部(臺北市:白馬精舍,民81年),頁418下。
註11:陳援庵,中國佛教史籍概論(臺北市:新文豐,民72年),頁22。僧傳中,「惠皎」與「慧皎」均指同一人,而此處亦同。
註12:(唐)釋道宣撰,續高僧傳,卷26,大正新修大藏經,第50卷史傳部(臺北市:白馬精舍,民81年),頁604中。
註13:關於唐時「藏」字亦作書櫥之義,參考白居易「香山寺新修經藏堂記」之文(參見:註55),即可證明。曾有學者認為前註引文中所提及的數字前後不符,而懷疑此記載的真實性,是故筆者特別說明之。
註14:(唐)白居易,「東林寺白氏文集記」,(清)董誥等編,全唐文,卷676,重編影印全唐文及拾遺,第3冊(臺北市:大化,民76年),頁3100上-中。
註15:(唐)白居易,「蘇州南禪院白氏文集記」,(清)董誥等編,全唐文,卷676,重編影印全唐文及拾遺,第3冊(臺北市:大化,民76年),頁3102上。
|
頁36 |
臺灣地區佛教圖書館發展之研究 |
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(2001.07) |
註16:嚴耕望,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(臺北市:聯經,民80年),頁312。
註17:(清)阮元,「杭州靈隱書藏記」,(清)潘衍桐撰,靈隱書藏紀事,武林掌故叢編,第10冊(臺北市:台聯國風,民56年),頁6635下。
註18:(清)石韞玉,「靈隱藏經碑」,(清)潘衍桐撰,靈隱書藏紀事,武林掌故叢編,第10冊(臺北市:台聯國風,民56年),頁6642下-6643上。
註19:(清)丁丙,「焦山藏書記」,李希泌、張椒華合編,中國古代藏書與近代圖書館史料:春秋至五四前後(北京市:中華,1982年),頁84。
註20:王河,「兩宋時期佛寺藏書考略」,江西社會科學1997年9期(1997年9月),頁59。
註21:陳援庵,明季滇黔佛教考,臺一版(臺北市:彙文堂,民76年),頁86。
註22:小川貫等著;譯叢編委會譯,大藏經的成立與變遷,世界佛學名著譯叢25(臺北縣:華宇,民73年),頁103。
註23:本碑文轉引自:李松,「北京法海寺」,張曼濤編,中國佛教寺塔史志,現代佛教學術叢刊59(臺北市:大乘文化,民66年),頁201。
註24:(宋)文彥博,「永福寺藏經記」,(清)徐品山修;(清)陸元鏸纂,介休縣志,卷12,中國方志叢書:華北地方434,第4冊,臺一版(臺北市:成文,民65年),頁972。
註25:林慮山,「北宋開寶藏 大般若經初印本的發現」,張曼濤編,大藏經研究彙編,下冊,現代佛教學術叢刊17(臺北市:大乘文化,民66年),頁155-156。
註26:(元)李謙,「元洞林寺藏經記」,(清)方履籛編,金石萃編補正,卷4,金石萃編續編二十一卷補正四卷,二版(臺北市:台聯國風,民62年),頁730-732。
註27:大明三藏聖教南藏目錄,大正新修法寶總目錄,第2卷(臺北市:白馬精舍,民81年),頁355下-359中。
註28:(明)釋元賢,「寶善庵請大藏經疏」,(清)釋道霈編,永覺元賢禪師廣錄,卷17,大藏新纂卍續藏經,第72卷諸宗著述部(臺北市:白馬精舍,出版年不詳),頁484中。
|
頁37 |
臺灣地區佛教圖書館發展之研究 |
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(2001.07) |
註29:(清)李仙根,「迦葉殿藏經記」,(清)師範纂,滇繫,冊5,中國方志叢書:華南地方139,第3冊,臺一版(臺北市:成文,民57年),頁785上。
註30:(清)釋儀潤證義,百丈清規證義記,卷6,大藏新纂卍續藏經,第63卷諸宗著述部(臺北市:白馬精舍,出版年不詳),頁447中-下。
註31:陳錫璋,鼓山湧泉寺掌故叢譚(臺南市:智者,民86年),頁133。
註32:方廣錩,佛教典籍百問,宗教文化叢書5,二版(高雄縣:佛光,民81年),頁174-190。
註33:(唐)釋道宣撰,大唐內典錄,卷8,大正新修大藏經,第55卷目錄部(臺北市:白馬精舍印經會,民81年),頁302中。
註34:方廣錩,佛教大藏經史:八~十世紀(北京市:中國社會科學,1991年),頁274-291。
註35:同前註,頁327-355。
註36:王重民,中國目錄學史論叢(北京市:中華,1984年),頁129-130。
註37:同註34,頁354。
註38:(明)釋祩宏撰,雲棲共住規約,附集,(明)王宇春等編,景印蓮池大師全集(雲棲法彙),第4冊(臺北市:中華佛教文化館,民62年),頁63左-64右。
註39:(元)釋德煇編,敕修百丈清規,卷4,大正新修大藏經,第48卷諸宗部(臺北市:白馬精舍,民81年),頁1131上。
註40:方廣錩,「敦煌藏經洞封閉原因之我見」,中國社會科學1991年5期(1991年9月),頁220。
註41:「萬歷初上天竺募修補藏經疏曰」,(清)釋廣賓纂,杭州上天竺講寺志,卷15,武林掌故叢編,第12冊(臺北市:台聯國風,民56年),頁7636上。
註42:同註30,卷5,頁441下。
註43:同註38,頁64右。
註44:(清)釋通問,「箬菴禪師兩序規約」,(清)杭世駿撰,理安寺志,卷6,武林掌故叢編,第1冊(臺北市:台聯國風,民56年),頁216下。
|
頁38 |
臺灣地區佛教圖書館發展之研究 |
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(2001.07) |
註45:李家駒,「我國古代圖書典藏管理的研究」(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,碩士論文,民75年6月),頁124。
註46:釋來果,高旻寺客堂規約,禪宗全書,第83冊清規部(臺北市:文殊,民79年),頁188-189。
註47:劉振明、梁朝玉合著,「九華山藏經樓佛經保護之謎」,中國檔案學會編,海峽兩岸檔案學術交流會論文集:中國檔案學會代表團(北京市:中國檔案學會,1998年),頁27。
註48:同註12,卷12,頁516中。
註49:同註34,頁111-112。
註50:方立天,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,中國人叢書8(臺北市:桂冠,民79年),頁167。
註51:黃運喜,「唐代中期的僧伽制度:兼論與其當代社會文化之互動關係」(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,博士論文,民86年6月),頁96。
註52:佐藤達玄著;釋見憨等譯,戒律在中國佛教的發展,下冊(嘉義市:香光書鄉,民86年),頁684-685。
註53:無著道忠撰,禪林象器箋,上冊,現代佛學大系6(臺北縣:彌勒,民71年),頁232下。
註54:同註30,頁444中。
註55:(唐)白居易,「香山寺新修經藏堂記」,(清)董誥等編,全唐文,卷676,重編影印全唐文及拾遺,第3冊(臺北市:大化,民76年),頁3099下-3100上。
註56:同註34,頁113。
註57:(明)釋通容述,叢林兩序須知,大藏新纂卍續藏經,第63卷諸宗著述部(臺北市:白馬精舍,出版年不詳),頁668中-下。
註58:(宋)釋宗賾集,重雕補註禪苑清規,卷3,大藏新纂卍續藏經,第63卷諸宗著述部(臺北市:白馬精舍,出版年不詳),頁532上-中。
註59 註59:戴儉,禪宗寺院建築布局初探(臺北市:明文,民80年),頁38。大宋諸
|
頁39 |
臺灣地區佛教圖書館發展之研究 |
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(2001.07) |
山圖又稱五山十剎圖、大宋名藍圖,相傳為日僧永平道元或徹通義介於入宋時所繪製,而現存於日本的繪卷抄本約有二、三十種。
註60:同註39,頁1131上-中。
註61:(宋)釋宗壽集,入眾日用,大藏新纂卍續藏經,第63卷諸宗著述部(臺北市:白馬精舍,出版年不詳),頁557下。
註62:同註30,頁444中。
註63:同註38,頁64右-左。
註64:同註30,卷5,頁442上。
註65:釋太虛,「太虛自傳」,釋印順等編,太虛大師全書,精裝第29冊:雜藏:文叢,二版(臺北市:太虛大師全書影印委員會,民59年),頁186-187。
註66:曹仕邦,中國沙門外學的研究:漢末至五代,中華佛學研究所論叢2(臺北市:東初,民83年),頁18-19。
註67:同註58,卷6,頁538下。
註68:(元)吉剌實思,「捨田看閱大藏經誌」,(明)李翥輯,玉岑山慧因高麗華嚴教寺志,卷7,武林掌故叢編,第1冊(臺北市:台聯國風,民56年),頁484上。
註69:黃敏枝,(微片,NSC86-2411-H007-007)再論宋代寺院的轉輪藏(臺北市: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微縮小組製作,民86年),頁1。
註70:(宋)李誡撰,營造法式,卷32,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,第673冊史部政書類(臺北市:臺灣商務,民72年),頁673下。
註71:(唐)樓穎撰,善慧大士語錄,卷1,大藏新纂卍續藏經,第69卷諸宗著述部(臺北市:白馬精舍,出版年不詳),頁109下。
註72:張勇,傅大士研究,中華佛學研究所論叢19(臺北市:法鼓文化,民88年),頁428-434。
註73:王子舟,「公元五至六世紀:南北朝佛教藏書(下)」,內蒙古圖書館工作1992年1、2合期(1992年5月),頁59。
註74:(宋)葉夢得,建康集,卷4,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,第1129冊集部別集類
|
頁40 |
臺灣地區佛教圖書館發展之研究 |
天主教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(2001.07) |
(臺北市:臺灣商務,民72年),頁616上。
註75:同註69,頁1-2。
註76:(唐)姚思廉撰,梁書,卷50,臺一版(臺北市:鼎文,民64年),頁710。
註77:嚴耕望,「唐人多讀書山寺」,大陸雜誌2卷4期(民40年2月),頁33。
註78:同註21,頁118-119。
註79:(明)徐宏祖,徐霞客遊記,卷6上,第4冊,萬有文庫薈要992,臺一版(臺北市:臺灣商務,民54年),頁28。